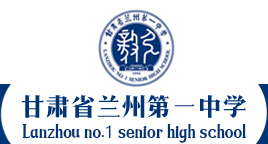我在这一段校史中上学
1943届校友、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 何天祥
(选自《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九十校庆诗文选辑》)
人人都说中学教育在一生中最重要,我充分相信这一点。
1937年,抗战开始的那一年,我虚岁十二,从小学毕业。毕业时老师说我成绩好,使我十分骄傲,当时正是抗日军兴,全国上下,群情激昂,我也非常兴奋。总觉得自己应该考进全省最负盛名的兰州中学。谁知道一榜发布,我竟名落孙山。受到了屈辱,又遭到父亲的斥责,我感到无论到那里,都抬不起头来。就在这个时期,街上看见了兰州中学招收“初—特别班”的广告。所谓“特别”,是每年交纳四块大洋的学费。父亲说:“交就交吧,可是这一次再不要掉下来。”不知是我用了些功,还是学校降低了要求,我居然考上了,总算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补偿与藉慰。可是还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难受,我在“特别班”里!
学校对这个特别班,给予了“特别”的照顾,安排了一些最好的教师,当时的教务主任苟秉元先后教我们的数学,后来当了师大、兰大教授的王近仁先生,教我们的英语,王先生的特异教学方法,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那时节,抗日战争发展得很快,不几多时候,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庄、太原相继失守,日本人一直攻占了山西运城,兰州成了国际援华线上的重镇,也成了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。起初学校安排在校内上两节课以后,就到野外去防空,边防空边上课。所谓野外,就是现在的甘肃日报社那一带。虽说是这样动荡的安排,我们的课还是挺认真的,在野外围着老师坐在树底下,依旧是英语、数学。直上到太阳爬到四墩坪的时候,才放学回家。
当时我是全校最小的一个学生,我有个舅舅叫龚得福,上兰中高二,他受了我父亲的委托,给学校说我年龄太小,让我住在他的斋房宿舍里。因此我认识了高中的大同学,或许是老师在他们班上夸奖过我,他们都争着要看我的英语练习本,都说我幸运,碰上了好老师,鼓励我好好学。这种来自大同学的鼓励,往往胜过老师的夸奖,胜过家长的训斥,我就格外努力,对英语愈来愈产生更大的兴趣。
抗日救亡的气氛越来越浓,第一个学期完了,又过了一个寒假,我认识的高班大同学中有好几位不见了,他们是杨希真(杨静仁)、陈定邦、安鼎铭,我们班上也有个陆广林不见了,听说走了陕北,抗日去了。
我们班不再叫特别班了,我们也不再交那四块大洋。
这时候,学校里常来一个送《大公报》兼送豆浆的人,大个子,瘦瘦的。一条扁担,前后两个小木箱,木板箱又用木板隔成小格子,装着热豆浆的小瓶胆。我认识他,因为他喜欢摸摸我的头,夸奖我两句。后来,听说就是他给大同学们送来了进步书报,可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什么东西,或许是嫌我太稚气。
日本飞机轰炸兰州的次数加多了。有时候,一天之内要来好几次,第一次把炸弹丟到陕西义园,就是今天兰大研究生楼那地方,以后就命中兰州城。古老破旧的兰州经不住狂轰滥炸,早已是遍体鳞伤了。学校就不能再到中山林去防空了,要迁校洮沙县的辛甸镇。放假回家,我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服务团和宣传队作救亡工作。
最使我兴奋的是这样一件事,有一天我正去服务团的路上,遇上空袭警报,我和同学冯云跑上了白塔山,刚爬进现在东面那座三角亭附近的防空壕里,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兰州城的上空,黑压压的一大片。白塔山上的高射炮响了,震得地摇山动,但敌机的阵式没有改变,突然一个个降低一下,又飞了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刻,兰州城里升起一排一排浓黑的烟柱,投弹原来是这个样子。看见这个景象,胸口郁气,又闷又胀,真是难受。忽然有人在喊: “两架”,“两架”,应声抬头,果然有两架敌机托着长长的烟尾,我才发现在敌机的阵式中,有我们油绿的小飞机在穿梭。正在这时候,这两架中的一架,打起转儿来,映着阳光一闪一闪的。另一架像夜空的流星,一头朝西氽了下去。防空壕里的人都跳出来了,顾不得什么危险,蹦起来了,大声喊:“两架,两架”。我胸口的痛闷霎时间没有了,这是狂欢。我亲眼看见了抗日战争,我亲眼看见了一场战斗,我亲眼看见了中国人的胜利。警报解除,我兴奋地跑回家去,要告诉家人我看见的一切,但是他们已经拿到了油印号外,击落的敌机,不是两架,而是九架。第二天敌机又来了,它想报复,但是又给打下了六架。我心里也在暗暗立志,我也要好好学习,长大为中国争气。
学校迁到了辛甸,这是洮河边上的一个村镇,离兰州150华里,从兰州到那里要翻过七道梁,走两个半天的山沟路。辛甸是校长张香冰先生的家乡,要迁到那里去,是张校长拿的主意,当然在下面也有许多非议,但是张校长作得很决断。兰州中学是全省最大的学校,这样一个小镇那里搁得下,还是张香冰先生发挥他在地方上的威望,克服了许多困难。学校在镇上占了两座小庙:街北的关帝庙和街南尽头的龙王庙。残破的神殿当教室、宿舍两用,另外又租用了南北两家住客的小店,作为学生宿舍,北头张家店的店主张爷有些江湖义气,南头桑家店的桑爷,夸口他的店里住过外国人,原来瑞典考古家安特生曾经住过他的客店,发掘了辛甸文化。
我有个堂兄,何天镇,和我一道上兰中,我们总是哥儿俩上学和回家。我们被分配住到关帝庙的上殿里,在住进去的那一天,我们看见两厢房里还停放着几口死人棺材。头一夜,殿角的风铃(铁马)叮当作响,我马上想起两厢房的棺材,害怕得没有睡着觉。
那时候的生活是苦的,但是思想里装着“抗战”两个字,什么苦也能顶得过去。对付生活上的“艰苦”,用的是“苦读”。爬在地铺上做作业,写日记,写作文,用树枝在地上练英文、演算题。天麻麻亮就要起床,起床以后,在门前的大车路上跑,晚上几个人围着一盏小油灯温课。后来过了很久,大家出力才在街后的荒地上平出了一个简易篮球场。
洮沙的辛甸镇、临洮的新添铺和宁定(今广和)的三甲集轮换集市,辛甸镇在逢集的日子里,窄窄的街道上车来人往,水泄不通,木板骨碌的大牛车,大红大绿的山里姑娘,大捆大捆的大葱白菜,真像莫泊桑在小说《一段绳子》的开头所描写的。背集的日子里,铺家都搭上门板,只有野狗在街上咬仗和觅食。
我们的学校生活也和集场的逢背密切关连着,择好逢集的日子,学校里组织学生在街头演文明戏,宣传抗日;还办献金台,为抗日募捐;开义卖场,为救亡筹款。你别看是十个小村镇,也别看都是些乡下人,真是人山人海,慷慨输将哩!
那时候有位数学老师叫成泮如先生,负责组织了一个文明戏戏班子,演出了滑稽戏《打城隍》,宣传破除迷信,《鸡大王》,宣传勤俭生产,捐钱抗日,这两个剧居然都成了保留节目,连着好多集日,都久演不衰。还有这么一次,在献金台的旁边捉住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,说他是汉奸,在捣乱,在破坏。于是赶集来的老百姓一下子都扑了上去,把那个学生压倒在地上,拳打脚踢。在旁的体育老师,还有几位学校的人急匆匆跑上前去,拉开了愤怒的群众,用绳子绑了汉奸嫌疑犯,说要送到县里去。群众们愤愤不平,不让放走,要就地处置。后来才听说这是一个活报剧之类的演出;原来那汉奸是同学扮的,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,那同学白挨一顿痛打,这还算好,没有遭到不测也算万幸,不过队这次冒险,倒反映出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!
学校里有位教生物的老师,高艺舟先生。他是日本留学生,他会画,他的大幅漫画刊载在武汉出刊的《漫画》上,有好几次哩!他负责组织了一个“兰中漫画工作队”,我也参加了这个队。我们每半月刊出一个彩色的漫画壁报,文字少,画幅多,贴在一块大木板上,赶逢集的日子,搬到街心里去展出,吸引了不少观众。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。今天回忆起来,我们还为《兰中漫画》的活动而骄傲。工作队里出了两位知名的画家,一位是轻工局的美术师谢笠,另一位是甘肃省有名的讽刺画家裴广铎。
我们的功课,并没有受到救亡活动的冲击,反而是经过激励,抓得更紧了,每天六个钟头的正课以外,还有课外活动,篮球最普遍,学生组织的球队很多,有名的是“兴中”和“乐群”。我们小同学差不多都喜欢踢毛弹(用毛线绕的小足球)。星期天,要不到街道南尽头,一条引洮灌田的渠头去游泳,就是到附近的各村镇去远足,我除了参加“兰中漫画工作队”以外,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考古队,在安特生发现辛店期彩陶的山坪上,去捡拾陶片,居然捡了一提包,后来一位上西大的历史系的大同学说,很有用,他完全拿去了。我们的学习生活,又紧张,又忙碌,兰州中学的学生像烧红的铁块,放在铁砧上,敲了这面,又打那面,不论打成一块铁锨,还是一苗蹄钉,都成了—个个有用的器件。
我在初中毕业前害了一场伤寒病,我堂兄和我搬到一家姓张的农户家,张奶为我做病号饭。我父亲因为事忙,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来看过我一星期,我的堂哥始终在我身边照料。老师和同学们的问候与安慰,都由我堂哥转给我。病好以后不久,就参加了初中毕业考试,或许是老师们对我的殊遇,我居然得了一个比较优异的记分。
战事仍然在进行着,生活依旧很苦,但是日机的空袭不那么频繁猖狂了。许多同学都转考到甘肃学院附中,因为这个学校在兰州城郊。但是我仍然留在辛甸,继续上兰州中学的高中。我妈曾经想要我换个近便的学校,我父亲说,“兰州中学是最好的学校,还是留在那里好。”说实在的,我的心理上一点也没有转学的念头。
我高中一年级的国文课,由校长张香冰先生亲自担任,课本用的是商务版傅东华编的,开头就是《古文辞类纂序》、《诗教》、《典论论文》等等,够艰深的了。想不到平日一本正经、面容严厉的张校长变成了国文教师张老师的时候,完全换了一个人。他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。我见他书上的眉批旁注,圈圈点点,整齐得很,我更欣赏他在我们作文后的毛笔批语,或指正,或奖誉,或鼓励,或批评,严谨无华,简明中肯,尤其是他那一手娟秀潇洒的毛笔字,简直是书法珍品。由于他的教学,我对对国文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第二年,我们的年级搬回了兰州的原校址,在校外,虽说是仍在战时,但气氛大大变了样,人心也不像前几年那样振奋,日机的空袭很少很少了。在校内,我们的课程变得既繁且重,一门数学分列成好几门。我成天埋头于赶作业。国文老师换成了张完夫先生,听说他曾经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里当过谘议,瘦弱矮小,文质彬彬。但是讲起课来,却变成一条生龙,一头活虎。他给我们讲了《多尔衮致史可法书》、《史可法复多尔衮书》、《项脊轩集序》、《左忠毅公轶事》等等。讲到慷慨悲壮的时候,他的精神激越振奋,讲到悲惨凄凉时,他的语调低沉婉约。听张老师的课,真是一个享受。他的讲课,对我以后学习英语朗读技巧,起了非常巨大的指导作用,我也在英语教学中,注意指导我的学生,运用正确的语调来表达文章的深层涵义。
1943年夏天,我从兰州中学高中毕业。在我升入大学的过程中,我走过许多弯路,也跌了一些跤子。究其原因,不外乎两点:兴趣太广,见异思迁。兴趣广泛是件好事,说明兰州中学的教育方向是多方位的发展,而不是偏重某几方面。见异思迁,则是我个人的事,正因为这个缺点,我没有显著的成就,有辱于我的母校,辜负了我的老师。
我的中学生活,正是贯穿着兰中迁校辛甸的这一段。对于兰州中学来说,这是不可忽略的一段,这一段正是八年抗战中的六、七年。
1971年,我有个急匆匆的机会,路过辛甸镇,我曾在旧校址上停立良久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追寻我的记忆,美丽的记忆。我想起了许多人,想到了我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的老师,我想到把客店腾出来让我们当宿舍的张爷,想到述说安特生故事的桑爷,想到塑造小中山林的张二爷,想到和我们一起参加升降旗仪式的杜大爷,也想到在湖北为抢运张自忠遗体而殉国的辛甸人宿团长……还有很多很多,他们都与我的中学生活分不开,是他们和我们共同编织了那一段时期的兰州中学,是他们和我自己塑造了我这个人的雏型。
转瞬间,五十多年过去了。我感激我的母校,我眷念,我珍贵我的那一段人生道路。